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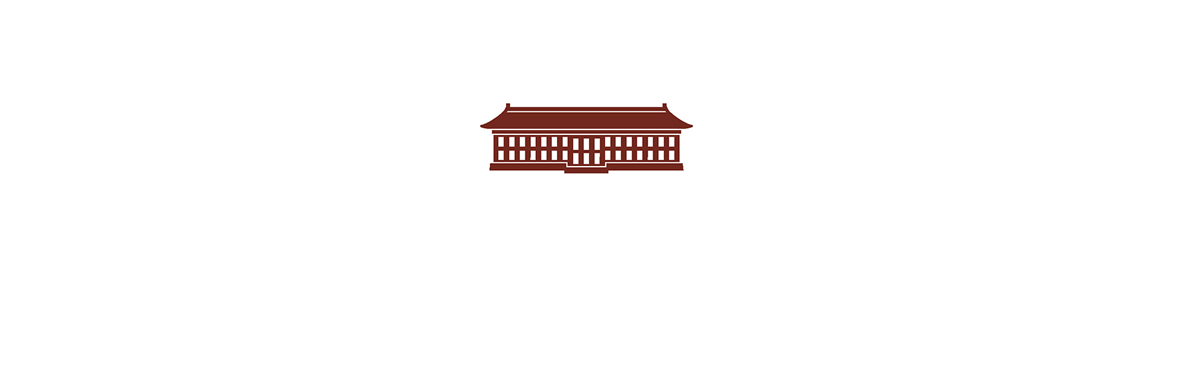


学业与学术

Q:学长一开始为何选择元培、选择PPE方向?
A:现在家里人都常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早在三四岁左右的时候,我出门常做的事情就是认读街边各种招牌上的字,他们经常把这与某种“早慧”联系在一起。想起这个说法还挺有趣的,我之后学习生活更多地还是受到我稍长一些时的养分的影响,而且我根本不是一个“慧”的人(笑)。
我从小爱好的东西还挺多的,看电视其实我也不怎么看动画片,而是蹲着科教频道、纪录片频道和新闻频道切着看,有几年忠实坚持收看《百家讲坛》《世界周刊》等节目。小时候我最大的爱好要数看地图,经常一看就入神,看完之后还会对着画,或者自己“架空”一个区域进行规划。我另一个知识来源是各种百科全书,从数理化到文史哲,从天文地理到古今中西,尽管我并非对每个学科都非常感兴趣,但至少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各个学科的常识性知识。这些知识的积累,不仅是见识性的,更是启发性的,对于我们联系地、全面地看待事物相当有帮助,也有利于我们建立一个对世界的整全认识——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可以说与之有相通之处。

朱江彬儿时家中张贴的地图
我的专业兴趣的焦点也相当丰富,并且经历不小的变化,但多少是有迹可循的。小学至初二是地理或城市规划;初三至高一时想学历史;从高二开始对国际政治感兴趣——北大国关也是高考时我的目标;高中毕业后至今,我也一直在学习法语。
高考时我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分数。在了解我的情况后,江西省招生组长胡少诚老师建议我将元培学院作为第一志愿,因为其中的PPE专业很适合我。所以事实上一开始元培吸引我的并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看到的若干炫目的招牌,而单纯地是PPE这个所谓的“王牌专业”。但某种意义上有些机缘巧合地确定了院系选择之后,后见之明而言我又确实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PPE确实满足了我对于跨学科学习的兴趣。

朱江彬大一关于PPE的整活
Q:学长兴趣如此广泛,是否产生过转专业想法?又是如何最终选择了PPE政治学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元培的制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A:我确实在大一下学期至大二上学期这段时间内很迷茫,产生过转专业的想法。一方面是个人因素:在政、经、哲之中,经济学的数学方法让我感到困难;我一直对哲学保有相当的亲和,但我个人会更倾向于更加有“实感”的讨论。尽管如此,政治学仍然让我产生疑虑的原因,则需要联系更加普适性的因素。如果说大一刚进大学时,每日勤恳地汲取新知识的过程能够为我们带来获得感,那么走过“入门”阶段之后,我们就很容易质疑:我每天确实好像在大学里面听了很多课,并且得到大量知识性的积累,但却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能怎么用——不管是以后走业务还是走学术。
但当时由于很难获得一个现在这样回溯性的认知,所以会把问题归结为专业不合适,然后便产生了换专业的想法。当时我想过要转纯政管,也想过要去学历史、法语或者外外,甚至一度下定决心要转国关并为此做了相当多准备。当然,也确实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在选课上进行了不少尝试,修读了许多上述专业的课程。这里便体现出元培的好处:我可以不选这个专业,但是我可以和对应院系同学一样平等地选课。这里也体现出PPE的好处:由于PPE的培养计划所含括的课程范围非常广,因此我的尝试成本也相对下降了。这个过程一方面充实了我自己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是让我知道这些学科到底学起来是什么样的,能帮助我更好地确定专业选择。在周游许久之后,我最终还是得出了PPE是最优解这一结论。

朱江彬在公共基础法语(一)、(三)的结课合照中
Q:看来学长的大学生活进入正轨也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请问能否多分享一些你在这方面的经验?
A:确实,不仅仅是专业选择问题,而是我在进入大学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生活的状态。我高中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愿意交往也确实结识非常多的好朋友——跟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些,比较“疯”、比较随性。但是在大一那段时间,我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状态中,不太敢去跟别人主动地聊天说话。比如在大一的讨论班上,我很少主动发言,即使发言一定都是“有精心设计过的”念稿。这段时间,包含着不自信,包含着知识储备确实不如别人的事实,但总体而言是一种精神的封闭,整体地导致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处境。
改变的关键是改变心态、打开精神。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普通,这是一切的前提。在此之下,如果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差距是难以否认的,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因此影响到自己的步调,不应该困在比较当中。要做的,一方面,提高自己,补足弱项;另一方面,拓宽视野,看到不同的领域,由此看到他人和自己的局限性,以及可能性!“赛道”有很多,我们总能在一条上具有比较优势。
至于我做了些什么。一方面是学业,学业的部分我在三学的采访中说过不少。这里我想补充的一点是一定要主动获取信息和拓宽视野。大学相较于高中,在我看来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所掌握的信息在各人之间是不均匀分布的,而在我的观察里,信息量往往与一个人在学习生活中的优势地位是强正相关的。因此,在学习知识之余,更重要的是从各种渠道获得信息,从朋友圈到公众号,从微博、豆瓣到B站、知乎……我们获取的信息不一定能裨益我们,我们阅读到的观点不一定能迎合我们,但他们都为我们多打开了世界的一个面向,而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必要的。
另一方面是人际交往。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从大一到大四,一路上结识了许多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也逐渐找回了曾经的自己。此外,与老师的交往非常重要,而说实话这是我在高中时较为轻视的——尽管我与所有中学科任老师的关系都很好,但我还是更愿意自己解决问题,而且我也不需要主动获取信息因为他们往往会直接给予我。而大学是不同的,显然需要我们自己发挥能动性。我记得大一时一位老师说自由提问“no stupid question”,这不是说“不可以提蠢问题”,而是说“没有问题是蠢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受用的。大学四年我遇到非常多优秀的关心或启发我的老师,但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位应该是可以说是我大学的第一位老师,政府管理学院的张健老师,他用一种相当鲜明个人特质的方式,教会我在事实与评判之间如何做出区分,我们所接受的成见是如何应当被质疑和重建的。
总体来看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高中的我看似相当成功,但那种其实被某种相当轻巧的成就感满足乃至骄纵的状态——不管是来自于成绩还是人际关系——事实上为大学生活埋下了雷点。当时的自己有一个在特定年龄和情境下非常宽广的外在面向,但内心世界却没有坚实地扎下根。恰恰我现在看到,在大学里重建一个良好的状态,则是要先回到自己,然后再去向外扩展。当你自己内心有足够的容量或者说能量,无论是看待问题还是与人交往都会多一份从容与谦和,而与此同时,许多曾经非常汲汲于的外在问题,诸如人际交往以及许多与世俗的评价标准相关的问题,反而迎刃而解了。

朱江彬入学的第一堂课——政治学概论(今名“政治学阶梯”)
Q:学长是如何选择学术的道路,确认对学术的热爱的?
A:我常常说,北大在空间上有一些与大学生活同构的特征,从最具标志性的西门走进去,我们正对着规整的花坛,中间是庄严的办公楼,就好像刚进大学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光明的。但是你穿过这个门之后,你会发现它岔开了非常多条路:往勺园的、往未名湖的、往外文楼的,往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常常讲高中与大学的区别:我们能在高中看到明确的起点和终点;而大学将各种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专业的选择,学工、社团、各种组织的选择,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等等。
如何确认你喜欢一样东西?某次李猛老师在开“元桌谈”的时候也谈了这个问题。我记得他的说法,简单来说就是看你快不快乐,这个快乐更多地包含一种满足感、获得感、成就感的面向。我想每个人都适于其自身的生活秩序,而生活方式本质上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对于一些人来说,一种更简单的、直线条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种心无旁骛的、有明确目标和规划的生活方式;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在完成必要的俗事之外仍然对时代的境况保持敏感,热爱探讨世界如何以及我们如何在世界中自处的问题。我没有自信说我选择了学术或我是个适合学术的人,但至少我自己会把自己划在前面说的后一种人。
当然,从事一种学术的、智性的或阅读的生活,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但至少我们能更具有接近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可能性。我今年年初读到的《回归故里》这本书给我很大的触动,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把自己作为方法”,我们学习再高深的理论,最终仍然要回到那些最初激励我们去思考的原初关切中去,要有对于现实的困惑与关切,这才是所谓“有生命力的学术”。所以回到更现实的问题上,确证自己的选择,需要发掘自己的兴趣,但更重要的一点或许还在于思考如何更好地将其与作为生活的“制作”或创造的过程相结合。如果是对学术感兴趣,对于本科生而言,那就应该将知识与灵感,通过尝试一些研究活动,比如挑战杯、本研之类,转化为切实的成果。我重拾对学习的自信,也是在本科期间跟着我的导师费海汀老师进行了一些研究之后达成的。如果仅仅局限于知识的摄取,不仅这些无法落实的知识会变得不牢固,哪怕我们的生活秩序也可能会受到挑战。我们总应该为我们的所学所思留下点什么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法]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

设计

Q:对于设计的兴趣来自于?
A: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这些东西,我幼儿园版本的志愿就是当画家,后来也产生过以后要好好钻研下设计的想法。我对设计的兴趣的来源,包括比如书籍的装帧、各种会徽,以及地图。小时候还经常自己尝试用笔或者用电脑的画图板设计。
其实地图和设计具有相似性。第一,它们都选择性地反映真实,抽象地处理信息。地图会根据其希望呈现的信息剥离掉很多层次,从而给出最集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地图上对于不同地理事物的填色和标号,从立体到平面的处理等,便是对原物的抽象乃至扭曲的展现。第二,它们都具有美术性与审美价值。例如,在地图上为什么要用不同但有限的颜色搭配,并且相邻行政区颜色不相同?这当然就涉及到地图的审美考虑。再如,有些地图显得很逼仄而有些则看起来赏心悦目,当时我便有一些朴素的认知,即这与线条的粗细、形制,颜色的数量、饱和度,印刷的材料和质量都有关系。
另一个是会徽,这是直接和设计相关的。关于我特别喜欢的徽标,我首推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现在如果上网搜所谓“失败会徽案例”,大概就是一些看上去乱七八糟的,一个图案中包含无数种颜色的徽标。这种徽标用来做高考语文题就很容易,各种元素和颜色都能传达某种理念,给分点很多。我的一个理论是,这与举办方对于设计者的干预程度有关,他们往往希望徽标的内容和寓意越丰富、越全面越好。因此这是一个平衡或考验,即内容的丰富程度往往与视觉的档次呈负相关。我们看2008年的奥运会徽,颜色上就是单纯的红色和白色,形制上规整大气且富有民族特色,寓意上包含了运动的人、北京的“京”、文明的文相当深重的内涵。这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好的设计的典范:既对信息保持克制,又极具审美价值,并且在意义方面有充裕的提供。

徽标设计的优秀案例(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和失败案例
Q:第一份设计作品是什么?是怎么做出来的?
A:小时候自己非常不专业地画过很多,现在我硬盘和家里的文件夹里都还留有不少。
但第一份正式的设计作品是地院海上钢琴师的电影票,这是那年元培和光华合办的男生节观影活动的周边。我的设计灵感来自电影中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也被我理解为全片戏剧冲突彰显得最充分的一幕:男主要在下船与留在船上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他站在走了一半的舷梯上,与心爱的女生安定在城市中,还是继续海上无尽的独身生活?这是一个问题。受到《寄生虫》一幅经典的海报的启发——富人的生活与穷人的生活分别在楼梯两侧——我又引入了一个改进:在既有的舷梯下面加一个倒过来的舷梯,一面是他向下走向城市,一面是他向上走回船。然而,这个设计有些太“满”:设计师想传递的东西可能会非常多,但是最终应该做出取舍。第一是因为要传递的意义太多往往会牺牲掉画面的整齐和简洁;第二是需要让读者有自己的想象空间,作者的产出和读者的诠释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文艺创作过程。最后,在设计组的凌峰、文杰学长和其他伙伴们的建议下,我做出了删改,并且将删去的元素运用在了电影票的背面,而这个形象也点了活动的“脱单”的题。
这是我的第一个设计,此前我甚至连PS都没怎么接触过,但在设计组各位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竟然很快地具备了将自己的设想变为现成的设计的能力,还收获了将其落实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打印品并将作品分发到同学们手中的满足感。

地院放映《海上钢琴师》影票的诞生
Q:学长在上个学年曾经担任设计组的负责人,能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设计组的工作?
A:设计组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形象标识方面,设计组推出原创卡通形象并将其应用于书院各处,创造共同文化空间;设计组日常更新35楼门厅水牌,推出书院主题系列印账,记录书院成员的生活点滴;设计组还与各部门组织合作,设计标志或视觉系统,设计宣传海报。第二,空间改造方面。设计组推出许愿墙为书院成员提供交流表达的平台,并负责日常维护和宣传;设计组充分利用公共墙体,宣传书院活动、展示学生风采,并深度参与公共空间改造。第三,文创产品方面。设计组设计纪念衫、纪念帽、主题贴纸、马克杯、徽章、明信片等产品;设计组为学院、书院以及各部门、组织提供文创设计方面的协助,重要合作方包括元培地下电影院、元培书房、元气咖啡厅等。

叁拾伍圆设计实验室(元培学生设计组)2022年宣传册
Q:学长对设计组中哪项工作感触最深?最近是否有重点推进的项目?
A:最有感触的工作是许愿墙。许愿墙的设置与所谓“内卷”的环境有关,内卷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同学们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向出现不适或者迷茫。我们的想法是提供一个排解的窗口,让大家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学习和生活的情绪或者观点。那么相较于自媒体或者校园论坛,许愿墙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它具有匿名性,当然这个是相对于朋友圈而言的,它不会暴露表达出的困扰后面的主体是谁,有利于让大家更加的畅所欲言。第二,与北大树洞相比,它的消息量是相对有限的,许愿签的更新基本上以一个月为周期,可以让每一种意见更加持续和充分地被大家看到。第三,公共性、私人性、互动性的微妙平衡,因为写许愿签的人本质上是默认要将想法展示给大家看的,虽然观看者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希望告诉大家自己存在这个问题,并且在某些时候,我们还能看到有热心的路人给他加油打气或提供建议。第四,许愿墙是专属于元培的,它传递的信息是:在这方书院空间里没有人是孤独的,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困扰,但这些困扰是公共的或共享的,我们是可以在其中找到共鸣的,有利于我们书院共同文化的营造。第五,潜在的创造性,我们在日常整理许愿签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许多人把我们的许愿签当成画纸在上面进行艺术创作,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文学大师”们创作的非常有意思的段子或吐槽,此外签与签之间也偶尔能碰撞出交流的火花(可以参见设计组公众号的文章)。总之,透过许愿签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书院作为共同体的文化营造的侧面,世代的困顿也许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课题,但在每日的匆忙之间我们仍然能看到那些灵光一现的时刻,脆弱情绪的流露,更重要的是,可资共享、参考和共情的境遇与经验。

由设计组负责运营的35楼许愿墙
我们近期一个重要的机制创新是对每楼层每侧盥洗室门口的空白墙面进行利用。此前,我们在许愿墙进行了白墙利用的意见征集,我们的计划是结合设计组的自身想法和同学们的诉求列出一个清单,清单中将包括可以在白墙上添置的物件。待确定之后,我们会在各个片区发布问卷,由各个片区的同学投票决定添置哪一项设施。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很良性,它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学院、作为学生组织的设计组以及学生这三者之间在话语权上的平衡:这个提议和活动的框架是我们搭建的,具体意见是同学给的,在意见中我们又加入了设计组和学院的想法,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学生,而且是分片区不同的决策。具体的成果应该在不远的将来就能与大家见面,而这个征集过程我们也将在未来持续进行下去。

生活

Q:学长平时一般做什么?看电影和听音乐方面有没有什么偏好?
A:我是个特别好玩(大概也特别好玩!)的人。一般来说,除非我有火烧眉毛的事情要完成,否则朋友的邀约我都是会答应的,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聚餐、观展、看电影、逛公园、喝酒等等,当然对于我来说哪怕仅仅是和朋友什么都不做,侃天侃地上几个小时,我也觉得很满足不会疲倦。
电影的选择我还是倾向于更有文艺特点的。我不爱看商业化太浓重的电影,尽管剧情足够精彩,但可能是人物设定的原因,它们往往无法让我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我喜欢的电影,大概多是讲普通人的故事的电影,能够让我在其中照见自己的影子。前段时间看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就是这样,探讨了一位其实没有那么糟糕的自认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如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和抉择。之前看到过一部非常喜欢的电影叫《将来的事》,影片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镜头让我非常触动:女主拿着电话在海边的泥泞滩上踉踉跄跄地找信号,女主自以为“我拥有满满的知性生活,这已经足以让我幸福”,但最终发觉这并不是真的——而这相当程度上是我以及我相信非常多北大的朋友们的生活境况。所以这么想来,其实我喜欢的电影更重要在于应当传达某种信息,在所有电影台词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来自《戏梦巴黎》里的“A petition is a poem, a poem is a petition”,任何文艺作品都应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朱江彬最喜爱的10部(大学后观看的)电影
我想如果有人问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热爱是什么,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音乐。我听音乐听得非常多,目前在豆瓣标过600多张专辑,可能不如一些专业人士,但也是相当可观的数字。我听歌一般都是以专辑为单位去听,因为我认为专辑才构成音乐的一个完整的单位。我主要涉猎的是华语和英语世界的(广义的)流行音乐,以女性音乐人的作品为主。高中时听以当代欧美流行乐为主,大学之后则开始欣赏上世纪的欧美音乐,而且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世纪之交前后的华语乐坛的精彩。我所最爱的那些音乐人和作品,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深刻地塑造了我的灵魂。我非常爱托歌词来抒发感情,以至于我一位朋友曾经打趣地说:“你成为一个好人的前提是不再引用歌词来指涉自己。”确实,一首重要的歌往往会与初听或循环这首歌的那个时候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联系在一起,这是某种通感。一首好的歌总是有持续的生命力,有让我走在路上想要跟着哼唱甚至扭动的冲动,或是有在深夜时分让人心绪翻滚或沉寂的写实感。最后,也感谢音乐,让我认识了相当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朱江彬的手机壁纸(由他最喜爱的音乐专辑制作而成)
Q:学长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热爱摄影,也热爱记录,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怎样的?
A:我爸妈经常说我是个“特别爱留垃圾的人”。确实,在我家里的储藏柜里躺着我从幼儿园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课本、资料和物件。当我朋友要把某样在我看来应该收藏的东西扔掉的时候,我都会说:“留着!等我们80岁的时候拿出来哭。”
这些都和我对于生活的态度有关系。我的理念是:好的,坏的,我都照单全收。有时我会和一些朋友在一些问题上不太一样,比如,对于一段可能相当不具前景的感情,许多朋友的态度是应该保护好自己,而我的态度则是如果感受到了爱的冲动,那么便应该遵从自己的直觉,即便最后是伤心,那也是一段有话可说的经历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再比如,对于一段可能不堪回首的时光,许多朋友的态度是删照片,丢东西,清空聊天记录和相关动态,把相关的人和事都从记忆中抹去,而我的态度则是,恰恰应该记住所有的遗憾和痛苦,让相关的物件和印象都好好地存在于我们的储藏空间和大脑容量中。我们所经过的,都是财富,都是我们应该为之保持感触乃至感激的塑造了我们自己的东西。
因此便很好理解我的“收藏癖”——之所以这么说,或许是确实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至于我现在家里的储存空间相当告急,我的手机储存空间也是如此,我的Apple ID用了四年多,目前已经攒了50000多张图片。从日常的人像和风景照,到每一餐吃过的东西,到喜欢的文字和表情包,到有意思的随手生活片段,到网上看到的具有象征意义或历史意义的图片,乃至到朋友的好看的照片和重要的人生事件。我的社交软件也是如此,我常常有超乎常人的表达欲,以至于一天发布几十条动态都是家常便饭(笑),内容往往仅仅是一瞬间闪过心头的想法,或者是一句喜欢的歌词,这些便是我的日记。当我未来某一天怀旧时,便能回头找到某天某时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中回头看或许只能看到一个幼稚的自己,但某种意义上那也是成长的见证,是活着的印记。

2020年结束时朱江彬用当年重要照片拼成的纪念图
Q:学长的生活态度对于你的工作或学习有没有什么帮助或影响?
A:记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其实与我个人关于书院建设的理念有关。书院建设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希望触及每个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响应它。事实上,书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可见的、静默的、缺乏声量的,我们当然希望把这些人都调动起来,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我这里,一个理念就是:让每个人都出场,即使是以一种最低形式的出场,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记录”。我对生活的记录,不需要多么郑重其事,可能只是一时的目光交错或者突发奇想的随手记录,我用这样的方式让我生活的每一个棱角、褶皱都以一种最低程度的方式记录下来。我觉得书院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维度也是这样,相较于活动、项目、设计等比较隆重、比较煞有介事的书院建设,我所说的是:许愿墙上的每一句话、宿舍门口的每一张名牌、书院建设中的每一次投票——让每一个人都在元培生活过之后留下一些痕迹。

朱江彬作为元培住宿辅导员的造型照
经过者皆为应当珍贵者,这个理念也帮助我度过了许多难过的时候。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长期以来不愿意接触业界而只是想待在学校里的想法,其实并不能让我逃开那些我藉此想要逃避的负面,无论在哪里,每个人都要面对类似的课题:如何与同事交往,如何完成上级的要求,如何组织一场活动等等。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面对困难或如何完成任务,而在于如何看待这些焦虑、压力。生命中是有普遍联系在的,今年我很喜欢的一部片子《蓝白红之红》里传达的一种世界观就是这样,人在某个时刻的遭遇可能便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将来的走向。延展出去说,与人交往是如此,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个他人时所传达出的善意,不应该总是功利性或目的性,说不定某个时候,我们种下的善意就可能受到回馈,你与某个交会者能够通过某种机缘成为伙伴或恋人。回过来说,我们所熬过的劳苦,不管是科研或者学工,综测加分、奖学金、人脉资源等当然都是我们去做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使最后没有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回看的时候也不会后悔,它们至少让自己获得了一些什么东西。
Q:和学长交流到这里,总体看起来你有着一种非常轻快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你认为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什么?
A:保持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每个人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和适应方法。坦白而言我是一个不那么“稳定”的人,我和璐瑶学姐聊道:有的人是机关枪,可以持续地高密度输出;有的人像乌龟,慢慢悠悠地但言出必为精品;但我的特点是水平方差不小,状态常有波动,但总体而言较为平均,不高不低。对我来说,如何在波峰波谷中进行适当的、及时的排解和调适就非常重要。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一般会和朋友大聊特聊,或者在社交软件上“喷泄式地”发布文字,或者单纯地喝酒唱歌或大喊大叫,让脑子里紧绷的弦偶尔放松。其实这些对于现实的问题并不是一种解决,因为第二天我们仍然要好好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但这些方法其实无意中会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会更加乐观乃至戏谑地去看待我们遇到的困难,由此可能更平常心地面对自身的波动。当然,我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任何问题都没有一定之词。
因此这里涉及到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自我认知的问题。诚然当前各方面的竞争压力和社会环境都不是非常乐观,但内卷困境的一个主观原因或许还在于同学们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在以北大为代表的顶端的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中,学生们追求着事实上内容并不明确的超高的目标,伴随着这种“鸢飞戾天”的眼光,学生事实上走向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似乎除了大厂和顶校之外便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委身”,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应该接受自己的“平凡”——其实相较于社会中的大多数其他人,我们完全并不平凡——接受一个比预期低的自己,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能否达成目标其实受到许多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事实便是这些因素正在让我们面临所谓的“失败”的概率和风险越来越大,因此,没有必要过分地苛责自己。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生活的得失完全寄于那些乃至被符号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就,在我看来,而应该注重内心世界的培育,保持好奇,且行且思,形成属于自己的坚强的、自主的宇宙,我们内心世界越充实,面对外在的高高低低,我们才能在变动的时代里保持一份定力。
伏尔泰说“必须耕种自己的花园”,他提出这一观点的动因是希望摧毁他的时代对于人类理性、科技进步、爱情与信仰的乐观主义,而认为人们应该保持与世界的“安全距离”。我想对于所有同学,特别是元培学院的同学来说,“园艺培育”是一个值得重视且相当有意思的意象:培育我们自己的花园,看似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简单事情,与我们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或许不甚相配;但其实这不是微不足道的消遣,它是一种保护我们免受外在世界的混乱和危险影响的方式,能够将我们的精力集中在我们所渴望的良善事务上。

朱江彬于2018、2022年在未名湖畔
